2021年5月14日晚,佛教学青年学者论坛在1929cc威尼斯会议室X8210顺利举行,此次论坛由1929cc威尼斯与1929cc威尼斯中国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系1929cc威尼斯“人文思跃”系列讲座之一。论坛共分四场,主讲人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祖荣、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雁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伍小劼,主持人由1929cc威尼斯讲师甘沁鑫担任,与谈人为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林健老师、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松蔚老师。1929cc威尼斯沈如泉副院长,吕鹏志、崔罡、吴杨、赵川、唐丽娟等老师,1929cc威尼斯科研处袁琳老师以及来自1929cc威尼斯、四川大学的数十位硕、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论坛。

“佛教中国化”举隅——净土观念的渊源与发展
论坛第一场由李想老师主讲。李想老师的演讲围绕着“净土”观念的产生与演变展开,尤其关注此观念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产生的新变化。净土宗与禅宗是当今中国佛教中最主流的两支,虽然净土宗出现较晚,但“净土”信仰从公元一世纪大乘佛教刚出现起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净”字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并不具备精神、宗教层面上的含义,仅为“空间整洁”之意,而“净”在梵文中所对应单词śuddha还可以指代远离烦恼的状态。此次讲座主题的两个核心问题也由此引出,一是宗教意义上的“净”是什么,二是“净土”是以何种标准构造。

净土信仰的出现受到了部派佛教时代过去佛、弥勒信仰、大众部“十方世界有佛说”以及大乘佛教功德回向等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熟知的阿弥陀佛净土之前,《道行般若经》等经中记载了一个过渡性的阿閦佛净土,二者的故事模型虽然相似,但阿閦佛净土中仍保留了很多早期的佛教传统,阿弥陀佛净土中则仅有部分北俱芦洲、拘舍婆提、欲界和色界天等早期佛教神话中超自然世界的元素。阿弥陀佛净土与大乘佛教佛塔信仰紧密关系,还可能受到印度本土神话和波斯宗教信仰的影响。但“净土”一词实际上是在汉译佛经中新出现的概念,印度佛典中只有“佛国”(buddhakṣetra-pariśuddhi)。日本学者藤田宏达认为鸠摩罗什于406年翻译的《维摩诘经》中“净佛国土”这一动宾结构在其同年所译另一部佛典《妙法莲华经》中演变为形容词-名词结构的“净土”以指称“佛国土”。而那体慧(Jan Nattier)、辛嶋静志等学者则认为是支谦错误地将“配置”(vyūha)和“净”(viśuddha或viśubha)混同译为“严净”,成为“净土”一词的重要来源。但李想老师认为vyūha和viśubha可能在历史上曾以共同的单词viyūbha书写,这使得“配置”与“净”成为这一单词同时拥有两层双关含义。竺法护、罗什、玄奘等人对支谦译法的沿用也可以证明支谦并非错误地混用了二者。辛嶋认为支谦是将buddhakṣetra-guṇavyūhālaṃkāra(严净佛土)一词中guṇavyūha(功德配置)译为“严净”,而李老师则认为“严”实际译自alamkāra(装饰、美化),实际上是将“严”字形容人打扮整洁的意思延伸到国家上,在后世更衍生出“庄严”一词。这两层含义在大乘佛教思想上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维摩诘经》中,佛土的庄严与佛土的清净是息息相关的,又进一步与心的清净紧密相关,不离“净”字远离烦恼的含义。净土思想与传统佛教间的张力正在于此,净土虽然由心净而来,但仍是一个外部的理想世界,寄托了古代印度人民对美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渴望和追求。《维摩诘经》中“随其心净,则国土净”是从菩萨的角度阐释“心净土净”的问题,而“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则说明不同福德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情状,如释迦牟尼成佛后的娑婆世界仍不“清净”。对此问题又可以参考《大般涅盘经》中悲心深重的菩萨舍净土而救度五浊恶世中的烦恼众生的说法,或是将其理解为《华严经》和《梵网经》中包含了娑婆世界的莲花藏世界系统。
最后,李想老师总结了“心净土净”与“净”字两层含义的关系,菩萨通过净心得到能接纳众生的清净佛国,而众生能看到的配置美好、功德庄严的佛国土。也正因如此,才在汉语中出现了“净土”概念,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讨论汉地净土的相关问题。
《说无垢称经疏》研究三题
论坛第二场,杨祖荣老师作了题为《〈说无垢称经疏〉研究三题》的报告。杨老师分别从《说无垢称经疏》的作者、《说无垢称经疏》对鸠摩罗什旧译《维摩诘所说经》的批评、《说无垢称经疏》与《维摩诘经》的注疏传统三个方面进行了讲授。杨祖荣老师首先介绍了《说无垢称经》,此经实为玄奘对《维摩诘经》(鸠摩罗什译)所作的一个新译本。而《说无垢称经疏》是玄奘弟子窥基在讲解旧译《维摩诘经》过程中逐步创作的注疏,又在较长的时间里反复修改最终完成的,其中涉及到了玄奘一系对罗什译本的批评。

其次,杨老师讲解了关于《说无垢称经疏》作者窥基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其名字的问题。窥基正名为“基”,此事已为学界共识,但学者们对于从“基”到“窥基”的转变则有不同观点。传统上一般以避讳解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在细节上各有不同意见,但均认为窥基“讳窥”是因宋人避讳唐玄宗本名而成,然此说难以解释为何选择略带贬义的“窥”字。另一种观点则因在玄奘译场中恰有两位担任“笔受”职位的僧人,一名窥、一名基,认为“窥基”可能是二人名字的连写。但限于史料不足,对此问题仍难下结论。接着,杨祖荣老师介绍的是窥基传记书写的问题。窥基之传记共计十三种,其中《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本》《心经幽赞·序》《成唯识论·后序》《唯识二十论·后序》《唐太宗皇帝御制基公赞记》五种撰于窥基在世之时。通过对比这些传记的内容可以发现,窥基的形象和其在玄奘译场中的地位是逐步被塑造建构出来的,未必是史实。
随后,杨祖荣老师讲授了窥基在《说无垢称经疏》中对鸠摩罗什所译旧经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批评是玄奘一系建立其新译权威和彰显自宗的重要举措。窥基对旧译的批评主要在对教名(即经名)、品名和具体内容三个方面上,如果要建立窥基的批评体系,那么又可以划分为对旧译译文的批评、对罗什本人的批评和对基于罗什旧译的注疏传统的解构三个层面。但实际上,窥基的批评或其所持的理由多不太充分,对罗什本人的贬低也更多是藉此消解其译本权威性。
最后,杨老师概括性介绍了《说无垢称经疏》与《维摩诘经》注疏传统间的关系。虽然窥基有非常强烈的解构罗什旧译注疏传统的意愿,但显然未能成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传统。所以在《说无垢称经疏》中可以看到解构与延续之间的张力。
“法缘宗族”:作为宋代曹洞宗的社会身份和组织模式
孔雁老师作了第三场演讲,题为《“法缘宗族”:作为宋代曹洞宗的社会身份和组织模式》。孔老师首先以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强调的血缘、地缘、法缘三种组织模式及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在《佛教“法缘宗族”研究:中国宗教组织模式探析》一书中对明清时期佛教法脉谱系宗族化问题的研究引入本场演讲的主题。孔老师认为,虽然不少专门研究宗族问题的学者并不承认宋代存在宗族,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这一视角引入宋代禅宗宗派研究中。

孔老师认为宋代曹洞宗其实是一个新崛起的法缘宗族,因而被爱荷华大学副教授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称为“新曹洞宗”。从曹洞宗复兴第一代的芙蓉道楷、大洪报恩开始,宗派身份就成为界定禅师身份的定位系统,是禅师个人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至宏智正觉、真歇清了时,这种新传统已非常明显。曹洞禅师的宗派认同实际上是以世俗宗族的“家风”形式展开的,其模仿世俗宗族进行祖统构建的行为也是禅宗儒家化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孔雁老师强调,曹洞禅师并未将祖统建构本身视为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应更关注这种举动的实际功能。在宋代士大夫为禅师语录所作序言中,首先便会介绍禅师本人的嗣法关系,可见在士大夫眼中,禅宗宗派是类同宗族的。而对于禅师们来说,其本人在曹洞宗“神圣家族”中的身份也是界定其社会身份的根本标准。
法缘宗族在僧团中得以发挥实际作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嗣法关系的建立,但嗣法关系并非是线性,而是错综复杂的,其构建也会随历史语境和禅师的个人认同、个人需求而转变。如慧照庆预从芙蓉道楷出家剃度,本与丹霞子淳同辈,后又嗣法于丹霞子淳,变成了丹霞子淳的晚辈,但其个人仍将自己视为道楷的弟子。在芙蓉道楷圆寂七年后,慧照庆预在大洪山任职时将道楷的尸骨从芙蓉湖迁至大洪山。莫舒特认为庆预藉此将道楷在大洪山的经历从一年夸大到五年,是为了强化与道楷的联系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但孔雁老师认为这是对文献的误读,庆预并未伪造道楷的经历,五年实际上是指庆预在大洪山的时间。这种法脉认同可能只是表现出庆预和道楷间的师生情谊更为深厚。接着,孔老师讲解了宋代曹洞宗这一新法缘宗族中的权利和义务。她认为在同一法脉中的僧人关系类同兄弟,互相帮助被视为责任和义务,属于常情;而超越法脉,帮助其他法脉的僧人则会被视为道德高尚之举。
随后,孔老师又阐述了法缘宗族和禅宗丛林十方制间的张力。曹洞宗的法脉运作实际上是在十方制下甲乙制剃度家族的一个变种,仅是将传承关系由“戒子”改换为“法子”,剃度仪式替换为出世嗣法的开堂仪式,将发展地点从同一律院内部换为了各地的十方丛林。这种模式虽然较为松散,但仍是一种“宗族”模式,仍能保证宗派内部的人脉网络和资源共享。虽然曹洞禅师多在十方丛林任职(甚至很多寺庙是从曹洞禅师时由甲乙寺改为十方丛林),但他们却仍能保证同法脉的僧人继承住持之位,其关键在于曹洞禅师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最后,孔雁老师简略介绍了曹洞法缘宗族中的地缘因素。曹洞宗禅师中存在大量四川人,可见在法缘之外,地缘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孔雁老师总结道,曹洞宗的法脉谱系不仅为禅师们提供了一个神圣家族的身份,也同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身份。士大夫也同样以类同世俗家族的方式来定位禅师。同时,法缘宗族也是一种组织模式,同一法脉谱系的长辈有责任提携后辈,而后辈也有义务赡养、安葬长辈。同一法缘宗族间的成员互相支持被视为一项重大的责任和义务,成员可以从中获取他们所需的社会资源和住持寺庙的机会。在十方丛林中的法脉运作模式实际上是甲乙寺的一个变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只不过没有甲乙寺那么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且一定要通过地方官员的影响才能在一间寺院中有序传承。
日本藏中土佚失疑伪经《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介绍与初步研究
论坛最后一场演讲,伍小劼老师分享了对于《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以下简称《度星经》)的研究。日本京都上京区临济宗寺院兴圣寺保存了较多平安时代的古写经。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就兴圣寺古写经作了一次调查,并出版《兴圣寺一切经调查报告书》,其中著录了《度星经》。曾有学者提出七寺本《招魂经》与东寺本《招魂经》是此《度星经》的一个小本。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根据东寺本《招魂经》题名《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确认了《招魂经》即是经录中所载《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

《度星经》首见于僧佑的记载,《法经录》也著录了此经,《开元释教录》等经录基本承袭了《法经录》中的说法。《招魂经》也见于《法经录》的记载,在众多经录中亦被称为《招魄经》《招魂魄经》等。《招魂经》《度星经》在中土均已佚失。兴圣寺藏《大灌顶经》卷第一首题《佛说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但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文献,除《度星经》外,还有《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诸比丘咒经》和《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同时,相较七寺本,东寺本《招魂经》中还有额外两条咒语,这两条咒语亦不见于兴圣寺本《度星经》。但仅以文字内容多寡认定《招魂经》为《度星经》小本,证据还不充足。更可能是此经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东寺本及七寺本的《招魂经》与《度星经》可能源自不同系统。
兴圣寺本《度星经》的重点在于列举了亡人所属的二十八宿的度星数,使其度脱地狱,并强调亡人不能复连生人。但因为文字简略,并未交代招魂度星经法的详细仪程,也未记载生人与亡人间的关系。但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戒经》中反复提及了一种超度亡人的“度星”仪式,可见在南北朝时期度星仪式已经在流行。同时,在《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中多处文字与兴圣寺本《度星经》相同。此外,《太上济度章赦》中“断绝复连章”明确注明“度星斋用”。结合这两部道经及《度星经》,我们可以知道度星斋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请道官上章使亡人不再复连生人。而《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更是多次提及了度星斋,并记载了度星斋的仪式过程和所用仪式文书。虽然在时间上与南北朝相距较远,但考虑到仪式传统的延续性,这些记载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南北朝时期的度星斋。
如前述,兴圣寺本《度星经》中抄录了三种不同文献,可能是因为其应对着不同的功能。《度星经》本身是为了安抚死者,解决复连生人的问题,其中的焦点是非正常死亡的亡人。而《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是解决横死鬼变化成精怪为恶的问题。如果将这两部经及相应仪式配合使用,则能构成一个中国佛教处理人死后灵魂问题的完整仪礼。
综上,《度星经》应有不同系统,东寺本与兴圣寺本间的关系还待研究;以目前的材料,还难以确定《招魂经》是《度星经》的小本;可以参照道经帮助我们认识度星招魂经法,补充其仪式过程;从南北朝至宋元,度星招魂经法自成系统,其内容随着时间逐渐丰富;度星招魂经法明显受道教影响,但若要进一步研究,还应多加搜集相关佛教材料;可以度星招魂经法和度星斋为线索,探讨度亡仪式的发展。
在每一场演讲结束后,主持人甘沁鑫老师均略加评议。几位主讲人同与谈人、参与师生就道教上清经中以“盛”代“净”、窥基进入玄奘译场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曹洞宗法脉传承中的经济因素、度星招魂经法与度星章的仪式原理是否相同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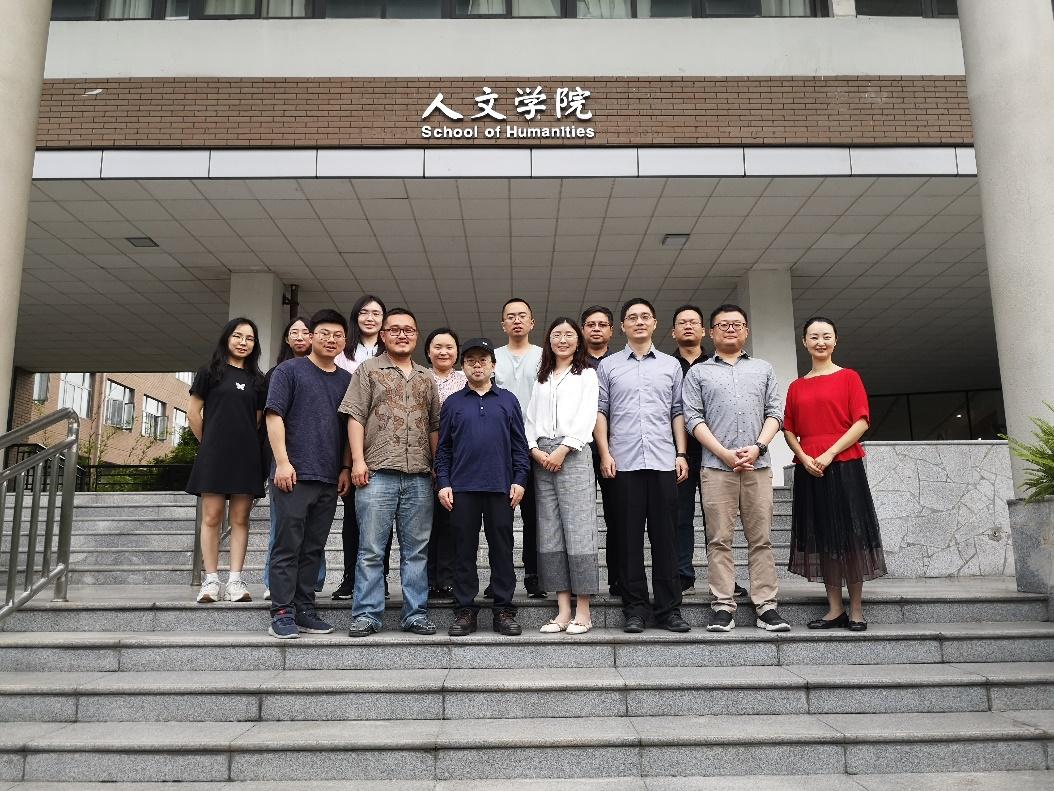
(撰稿:赵允嘉;审核:甘沁鑫)

